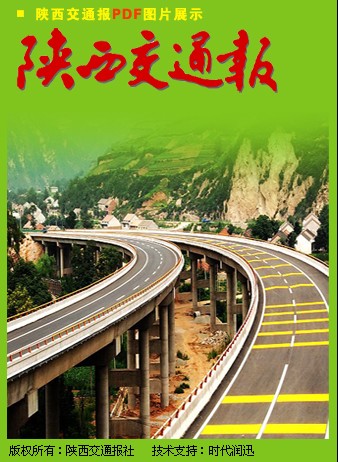母亲在世时,有一把又重又黑的剪子,早已锈迹斑斑,但她老人家一直舍不得丢弃,而是宝贝般珍惜。母亲六十岁时,我在远乡做一介小吏,回家为母亲祝寿,母亲满怀笑意地告诉我,这把剪子,就是用它剪断我们四姐弟的脐带,让我们离开母体,降临人间。她不愿丢弃,是因为这把剪子记录着我们的诞生。
满脸皱褶的母亲一句叨絮,我的心就慢慢飞翔起来,像一只鸟儿,在空空荡荡的苍穹。是的,多少年了,我们没有记住母亲生育我们的艰难,或是记得那样地模糊,那样地肤浅,仿佛母亲对我们的喂养,就是童年的玉米饭,就是童年母亲自染的布,手缝的衣,麻纳的鞋底。其实母亲的爱,就是从我们在母体中孕育时的那刻开始,每分每秒都是血和情。而我们忽略了那么多,想起来确实叫人惭愧。母亲珍藏那把旧剪子,就是珍藏她永远的爱心。而我们呢?
那时的乡下没有专门的助产医生,连接婆都少有。好多母亲在生孩子时丢了性命,悲哀就像出门的泥巴路,悠悠地让你无法躲避。我的母亲从五岁开始,就跟着大人干活,没有读过一天书,但练出了一身坚强。生我的大哥时,在没有奶奶和外婆帮助的家中,母亲就是用剪子,让大哥来到人世间。后来,父亲在大办钢铁时,去当了工人,母亲生我们仨姐弟,一样地是用那把旧剪子接生。
我小时候,家中的衣裤是母亲手缝的,鞋也是母亲做的,连冬天,母亲都要用旧布给我做顶帽子,两边各有一道耳帘,耳朵才不会被冻伤。这时,做女红的母亲用的是另一把剪子,有点短,很轻便。至于那把剪断我们脐带的剪子,则用一块旧的红平绒包着,压在箱子底,从不示外人。
到我读高中,就要离开家,到几十里外的县城时,母亲流着泪送我,心中充满着不忍。母亲从箱中拿出那把锈迹丛丛的剪子,反复摩挲,让人不敢问她为什么。这些细节对于只有十五岁的我,还无法体会母爱的深厚,直到母亲在1997年突然脑溢血去世,几近不惑之年的我才慢慢品出其中的滋味。
母爱时常是无语的,何况我的母亲没有读过一天书,口头表达能力本就简略,往往用“是”、“行”、“不”来表达。可是从她的举动中却能感受到满满的爱心。
我离开故乡到长江边求学,是1981年的秋天。川西农村刚刚包产到户,能吃饱饭。这时母亲发福了,宽宽的脸时时挂着笑。这次送我,她的脸上有了欣慰,毕竟我是我们黑水凼沟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母亲同样抚摸那把剪子,但没有多的言语,只是送了我差不多二十里路,看着客车滚滚载我远去。从车窗外回望,母亲还在目送我,手里仍是那把剪子。
我的孩子出生时,母亲从千里外赶来,为我们分担劳苦。更加衰老的母亲,看到了我女儿,那爱意浓浓地裹在眉头。这次她见到了医院是如何接生的,回来后讲那剪子,盘子,纱布,药水,当然母亲的表述不生动,充满好奇。她说,现在人太金贵了,哪像生我几姐弟,一把剪子就够了。
母亲弥留之际,再三嘱托我们,一定要用那把剪子来给她陪葬。我们答应了,母亲才落下最后一口气,走完73年苦难的历程。
那把剪子一定有魂灵,母亲在地下才不会寂寞。
那把剪子一定有生命,才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转达给母亲。
那把剪子一定有血肉,才能和母亲一样感受生活的苦辣酸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