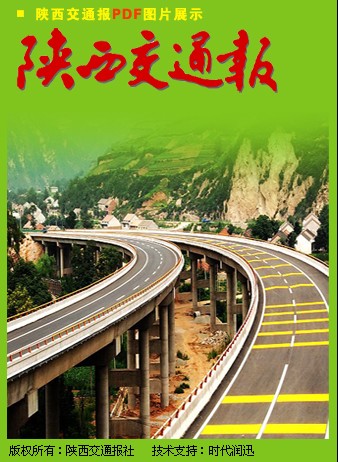事情发生在年少轻狂时节。
那一年,我17岁,刚参加工作,风华少年,意气风发。工作在矿山上,离县城30多公里。矿上的生活比较单调,除了上班没什么娱乐活动,整日间无所事事,闲暇时大多的时间便是看书。那时武侠小说正在流行,我们几个年轻人便疯狂地迷恋上了。有一段时间甚至渴望弄一本“武林秘笈”,以便也炼成绝世武功。
转变是在认识裴振学之后。
那天,我到同车间的老乡宿舍里去玩,一进门便看见几个人围着小桌子在喝酒。我老乡看见我就说:“来,兄弟,介绍一个哥哥给你认识。”然后,指着他对我说:“这是裴振学裴哥,矿上地测科的。”又对他说:“这是我小老乡,小李。”又招呼我拿筷子、凳子。席间,他们谈论的我听不懂:什么“老夫聊发少年狂”、“碧云天、黄叶地”、“杨柳岸晓风残月”等等。
后来熟了,便有事没事去他们那里,听他们谈诗论赋,好不羡慕。为了早日融入他们中间,费了一段时间狠背《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裴哥借我一本《历代名家词赏析》,看得出他对这本书的喜爱,可能他看了很多遍,上面有不同日子的读书眉批。他写的,有些看得懂,有些看不懂。他把书给我的时候,郑重地说看完要还的。为此,我买了一个笔记本,工工整整的将书从头到尾抄了一遍。在他们的熏陶下,逐渐知道了苏轼、辛弃疾、柳永,也逐渐知道了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田间以及席慕容、余光中、舒婷、北岛等诗人。
我对徐志摩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痴迷,我买了他不同版本的诗集、散文集、书信集,对他与陆小曼的爱情感动不已。18岁那年,我爱上了一个女孩,也被那个女孩爱上,很纯很真天翻地覆地浪漫了一回,最终还是独自一人在旷野上高唱潇洒地走。也就是那年在《陕西工人报》副刊上发表了第一首小诗,时过20多年了,到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每一句,甚至每一个字:背上简单的行囊/出发遥远的天边/来时没人迎/走时没人送/黑黑的夜/长长的路/不知要多久/管他呢/点燃自己的眸子/甚至血和肉/高声唱着/潇洒的往前走。裴振学知道后比我还激动,说值得庆贺,随邀朋喝友,聚在一起,热闹了一番。裴哥当时意气风发,朗诵了李白的“将进酒”,并郑重告诉我要好好努力。这首题为《潇洒地走》的小诗,挣了6元稿费,请客花了我60多元。当时我每月的工资也只是79元,以至于,大半个月我就在他们之间混吃混喝。
当时裴哥借给我很多书,我才有机会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再到《明清小说》,较为系统地浏览了一遍。同时也还送我一套《中国文学发展简史》,是大学中文系学生学习的教材,刘大杰主编,从右往左竖排繁体字版本的,于是,顺便也就学会了认繁体字。这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值得留恋与怀念的,也是对我后来影响最为深刻的日子。
我学会了学习,学会了鉴赏、也学会了做人。
后来我调回了老家,便与他们分开了。
那本《历代名家词赏析》,裴哥最后还是送给了我,现在这本书在上初中的女儿手里。女儿时常会问我以前的事情,“爸爸,伯伯们现在都好吗?”“好,都好。”感谢科技的发达,尽管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们还经常联系。
匆匆间,二十多年过去了,每当闲暇时我就会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我就会充满感动。
前不久,与裴哥电话联系,聊天的过程中他问我:“你现在还在写诗吗?”我说:“写,但仍然写不好”。他说:“写不好不要紧,只要坚持,一定能写好的。”我说:“年龄已过不惑,但总感觉不明白的更多。”他说:“还是太患得患失了。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其实,被动的接受,不如主动的承受,还是积极一些好、昂扬一些好。过程艰辛,结果不一定如人意,但至少可以说,我做了,我经历了,过程比结果更具有意义。”
我唯有诺诺。
生命因过程而精彩。
人生每一阶段都是可以也应该高歌的,无论是懵懂无知的少年,还是朝气蓬勃的青年,也无论是辛苦劳作的中年,抑或是安适闲逸的老年,痛苦与磨难,幸福与欢乐相辅相成。一个年龄有一个年龄的特点,在特定的年龄段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那样真实,无论对于错,都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只要真诚地付出了,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高歌,我如是认为。
(作者系商南收费站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