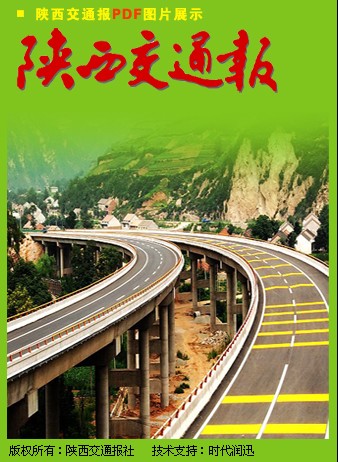从医院出来,太阳突然变得咄咄逼人,闪亮的光线变成一根根锋利的尖刀,在刘一梅身上刺啦刺啦地划。从医院门口踱到人行天桥,她就冒汗了。医生刚刚在她体内留下的伤口,开始翻江倒海般地传递着疼痛的信号。
“没事的,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已”。心里这样想着,可趔趄的身体,以及越来越剧烈的疼痛,突然一下子把这句话淹没了。原本以为生过孩子之后,疼痛已如蚊虫叮咬般无所谓,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就在走下天桥的那一瞬间,她的坚强被这疼痛彻底摧毁了。
等不到出租,她匆匆坐上一辆小三轮。就算是平坦的路面,不知怎的,那三轮却颠簸的不行。不到一站路的功夫,刘一梅又强硬地从三轮上下来了。
车费照付。在她下车的一瞬,她看到了三轮车主的窃笑和卸下负担的轻松。
一点一点踯躅到公交车站,像等待开往春天的列车一样,期待一辆可以回家的班车。疼痛迫使她蹲在地上,一边呻吟,一边张望。
好几辆出租车开过,却都说是要交班,匆匆驶过。终于有一辆车拉上了她,但车子却只能送她到半路上。
一上出租,她却再也不能忍耐自己的疼痛,一会儿向左倒去,一会儿像右倒去,呻吟一声大过一声。
“要不要给你家里打个电话?”
“不用了。没事。”
“哦――”。
又一阵呻吟。
家门打开的一瞬,刘一梅瘫倒在地上。
家是温暖的。倒下的那一瞬,有一个肩膀支着,可是,这疼痛却没有支撑。这预料之外的伤痛,只能自己一个人慢慢地挨。你渴望那么一点点的温暖和挂念,可那也只是渴望。爬到床头的孩子,还在渴望着你的温暖和担负。
生活就是这样么?怀抱远大的理想,坐落于平淡的日子。昨天你还在挤破脑袋对付一道挠人的高考数学题,今天你已觉得科学家的头衔是梦想之外的名词;昨天你还在大学校园里对一场突如其来的恋爱感动的稀里哗啦,今天却坐在一大堆尿布中间蓬头垢面;昨天你还在为受制于父母管制的不自由而郁闷,今天你却要为了生计,埋头于图纸之间,颠倒于加班的白天黑夜;昨天你还在幻想王子公主般高贵的自我个性的张扬与表达,今天你却清汤挂面,风风火火在不同的场所表达你的平庸与喧闹。
像肥皂泡,只在一指之间,破落无痕。
四月,万物蓬勃生长的季节,连空气里都流淌出一丝丝爱恋的味道。又一个周末,刘一梅从医院换药出来。一个熟悉的身影晃入眼帘。尽管十几年的时间间隔,可她还是认出了――同桌的他。
她知道他最近刚来的西安。为了什么,为了回到家乡的温暖,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初恋?他竟然卖掉房子,放弃诱人的工作,回到了这里。刘一梅觉得这可能与她有关,可是十几年的间隔,她在这个原因里的比例是不是应该可以忽略到无关紧要的地位,这一点,像一个答案在前面招手。
四月的阳光透过法国梧桐树叶摇落一地的斑斑点点,一如她对他斑驳的记忆,熟悉而陌生。前几天还在孩子耳边哼唱的“同桌的你”在耳边响起,可是,这变了的容颜和无从谈起的尴尬,却让这样的邂逅唐突而无味。
“人有的时候是要学着改变一下。不给自己机会,怎么知道就不行呢?”他依然是当年的意气风发。
而刘一梅呢,此刻哪怕一点点的改变,对她都是致命的。这十几年的时间段里幻想过的美丽的邂逅,却苍白的如同这白花花的日头。刘一梅突然在自己的身上看到了《飘》里面郝思嘉的影子。
“你动手术,你们家那一位咋没陪你?”他问。
“他要在家带孩子。”她仰起头顺口脱出。有一丝丝失落写在心里,却有无尽的高傲写在脸上。是的,迈进婚姻的门槛,房子、车子、孩子,有形的东西变成一种资本,在一个未来尚未知的人面前,她的高傲的的确确显示了门槛里面那个人的张扬。
短暂的沉默后,她们分道扬镳。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像那伤口长在你的身上,纵使蜜饯也不能替代你的疼痛。那被日子磨砺的模棱两可的爱情,又有什么可以让它新鲜如初呢?那些急急的等待你去做的事情,就算拥有父母的关爱,你也一样要一个人面对。没有什么可以挽救你的脆弱和孤单,唯有你,唯有你自己。小的时候,父母是越来越高大的大山,给你的心灵坚实的依靠;而现在,面对诸多的冰冷,你不仅仅要依靠你自己的温度取暖,还要把自己站立成一棵树,成为孩子、家人坚实的依靠。
站立成一棵树,以一棵树的姿态迎接这坚硬的现实。眼泪、汗水、孤单、冰冷,都要用明媚的微笑包裹起来,在心里把自己站立成一棵树,依靠自己的养分让自己风姿卓越,依靠自己的汲取让自己自信迷人。小鸟依人的姿态只会让自己可怜自己,而一棵树的姿态却可以强大到撑开一片天空,张扬每个季节里的丰茂与卓著。
(作者系省公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