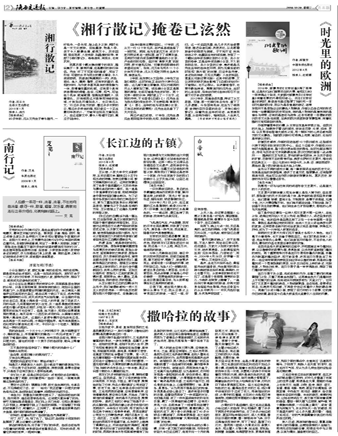作者:王以培
漓江出版社
2013年4月
【推荐理由】
王以培,人民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攻法国文学,翻译过《小王子》和兰波的诗集,发表过数篇小说、散文诗集和旅行札记。这样的背景注定了他骨子里深重的人文历史使命与慎终追远的诗人情怀。他一直是个未曾停歇的行走者,却被异域旅途中激发的回归意念鼓动。为了记录中华民族行将失传的三峡活态文化,更为了重拾民族身份认同的朝圣信仰,循着龙之子孙血脉流淌的方向,王以培踏上了这趟永无停歇的寻根之旅。
《长江边的古镇》系列是一套丛书,已出版四册,是王以培民族热忱和屈子情怀谱就的寻根巨制。王以培对这种活态文化遗产翔实的民族志式记录,以及散文诗般的优美笔触,皆使那些蜗居在现代都市,与文化之根疏离已久的城市浮游者们感受到来自长江古镇的清新空气。
所谓“圣地”,就是信仰的依托,心灵的归属。那些承载着深重苦难与深厚历史的亲切故园,那些从容淡定、坚韧勇敢的三峡移民,那些余韵悠远、历久弥新的民谣传说,皆使在都市快餐文化中窒息的我们,重新寻得自己的信仰。跟随王以培踏上朝圣之旅的我们,亦在行走中重新回归,找寻心灵的家园。正如王以培所说“那些沉入江底的家园,古镇村落,烟雨楼台,亲人墓地,正是我的圣地、我的信仰,我的根基。”
从王以培《长江边的古镇》系列丛书中,我们能清晰感知一种人文主义的历史使命:一种勾连历史故国与现代中国的尝试。在普遍处在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断层的当代中国社会,这种注重文化延续性的尝试弥足珍贵。这样一种从文化源头去发掘活态文化遗产,进而保存中华文化特异性、注重文化延续性的寻根之旅,帮助我们了解到这是怎样一个民族,作为该民族子孙的我们仰赖什么立于天地之间,让自己在精神上达到自足。
【精彩书摘】
一只灰燕穿过阴空。身边的水手戴着粘满油污的帆布手套,解开套在岸上的钢索,“观光2号”徐徐后退,随后向前,驶进碧绿的长江。
2004年2月2日上午,流过宜昌的江水是碧绿的;就像2002年1月1日早晨,流过重庆的江水是青色的。――就这样,清江连接了我的旅途;我有幸为此做见证。
……
飞机遇见气流,产生颠簸,我写的汉字也因此震颤,并恢复了它的元气,原本是一阵气流;我在高空,随春天的气息懒散飘流。
北京的太阳已落进暮霭,高空依旧阳光灿烂。北京今晚提前进入夜色,我的朋友们正驾车赶往什刹海,我还是一个人上路,再去万州,继续我的旅途。
今年二月醉倒在云阳,等云中的太阳将我扶起来,旧城已摇摇晃晃,撑不起旧梦;喝醉了,旅途戛然而止,或者说像一只落地的风筝,被风吹到江边;与老人们一起晒太阳,感觉比身边的老人更苍老,比浮云更苍白;而点点绿意,只能是心中依依垂柳……我要继续我的旅途――坐在云层里忽高忽低,与从前乘船漂流长江是同样的感受。
云层下面,就出现大群水母,群山从薄冰下过;我从云层之上审视自己的旅途,一程又一程,你没有走错。
上天入地,你还要去哪里?心愿之乡原本是一叶轻舟,漂到哪里,哪里就是故园;春夏秋冬至今如四个孩子,在江边等我。
向西飞,晚上七点一刻,天还是亮的;金红色的傍晚,小型飞机落在万州山顶,一出机舱,就吹到江边清凉的晚风。
“春风沉醉的晚上”,你不在酒吧,不在人群中,而站在江岸山顶;远远望去,万家灯火如变幻的象形文字,被夜雾浸湿。从前黄庭坚先生因“见长年荡桨,乃悟笔法”,而今,2004年4月28日,你带着一支笔,一颗心,又来到长江边。
是夜,坐在万州流杯池边,黄庭坚先生的塑像前,先生题写的西山碑今晚被锁在流杯亭里,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从前亭前的鲜花也不见了,还是那个卖烟酒、糖果的女孩儿,今晚趴在椅背上睡着了。一盏白炽灯照亮昔日的旅途,你再次起身向庭坚先生敬酒;先生还像至今仍从水中捞月――“中天月色好谁看,永夜角声悲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