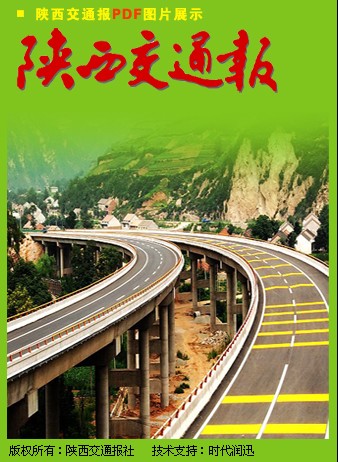李喜会,1995年至1998年第一届援藏行政干部,时任阿里交通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现任陕西省公路局路网调度中心主任。
当一个大雨瓢泼的早晨,记者对李喜会道明来意时,他手指在地图上的阿里划来划去,沉吟半晌说:“当年援藏走的时候,孩子才上小学,而今儿子已经娶妻成家。”为了更好地再现当时情景,记者用第一人称写下这些故事。
离开阿里已经14年了。
1995年,我刚39岁。中央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陕西省交通厅第一次派遣援藏干部。我到了阿里地区,担任交通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阿里,即使对于土生土长的西藏人也是相当陌生的,不仅由于空间上的阻隔,更源于艰难的道路交通条件。1995年,阿里境内只有从新疆叶城县通到普兰县的219国道的断头路。从阿里到拉萨,越野车走全是砂土路的国狮道,如果幸运的话4天可以到达。整个阿里地区只有一个养路段,在狮泉河镇借了四间房办公。阿里交通局是全国唯一没有自己办公室的地区交通局,和养路段一样借房办公,只有一辆越野车,连备用轮胎算上,五位领导每人才能摊上一个轮子。
临出发的时候,厅党组说――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今后,阿里交通局需要什么,我们就支援什么。
探路楚鲁松杰乡
扎达县楚鲁松杰乡位于阿里最西端,距离最近的印度守军只有一公里路程,可是,向内与阿里腹地无路可通。1991年冬天,那里爆发疫情,当地无法控制,大雪封山,消息根本无法传递到西藏自治区政府。最后经印度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告知中国政府,直到第二年6月,消息才传到阿里地区行署。阿里地方政府立即请求部队支援,用直升飞机将防疫人员送进去,但是死者已经掩埋,挽歌已经飘散,只剩下经幡在高原的风中猎猎飘荡。
1996年7月初,我带着工作组,配着半自动步枪,和扎达县的县委书记、县长一起从曲松区骑着马开始向楚鲁松杰乡进发。一路都是无人区,越往前走,离文明社会越远,回想起行署所在地――狮泉河镇,那可真算得上繁华大城市了。翻越海拔6300米的白色普布拉大山时,花草都不见了,只有雪线上齐膝深的积雪默然凝视。翻山根本就没路可辨,我们拽着马尾巴,四肢并用从陡直的马道挪步而上。爬两步,拽拽马尾巴,要马稍稍停下,容我们给自己换口气再爬。那一刻,马就是我们的上帝!在山顶,脸色发青的我们从怀里掏出哈达缠上五彩经幡,感谢苍天,终于拽着马尾巴上来了。
下山时我们依然死命拽着马,却是为了让“马儿呀,你慢些走”,那么陡的坡,一不小心就会连马带人翻下去。从山顶下山步行过几十公里的乱石坡,重新上马,天黑前顺山沟赶至一处有流水草地的深谷里。胡乱吃些烤焦的干馍,就地喝口雪水,展开睡袋就在红柳丛边露宿。高原的天空,星星格外明亮,马在四周悄悄地吃草,嬉戏。那会儿楞大胆,藏族干部说狼有那么多野生动物吃,不会拿人开荤,也就不知道害怕。不过,枪是不敢离手的。天亮冻醒时,睡袋已经被风吹来的积雪覆盖。翻身上马摇到傍晚,伴着马铃叮当,在金黄的夕阳下,终于望见了远远的玛尼堆,进入了楚鲁松杰乡,结束了我们两天140多公里的跋涉。我们是第一支进入该乡的汉人队伍,没有想象中的欢呼雀跃,那些乡民只是远远看着我们,露出欣喜羞涩的笑容。
当天晚上在头人的毡房里设宴,乡人礼数不多,却一律恭敬。进了毡房先向头人叩首,再来向我们问候。无论大人孩子,若是上来握手,戴毡帽的必先脱帽,双手在衣襟上迅速擦擦,谦卑地向我们伸来。听说要修路,藏民们喜极而舞,纷纷要求招待客人,拿出用牛粪火烤得发黑的藏小麦饼子,将野菜在带泥沙的冰川融水中清洗做熟,最终还是带着沙,黑黑的一团端上来。
根据勘察情况,我们回到狮河镇做了两个方案。马不停蹄开车向当时同是援藏干部,挂职在西藏自治区交通厅任副厅长的冯正霖汇报,同时争取到了陕西省和河北省的资金支持,当地政府以工代赈,开始修路。从此,楚鲁松杰乡结束了没有路的日子。
三个轮子换货车
一年以后,我已经被称为阿里地区公路的“活地图”。成天与阿里地区的狂风斗、融水斗,为了防止水毁路面,修融水导流坝,修过水路面,各种穷办法简直想到了天尽头。自己的驾驶技术越来越高,经常从齐挡风玻璃的河水里穿过,过戈壁滩更是小菜一碟,天天实践“紧过沙子慢过水”的经验,还培养了好几个驾驶员。
有一次,冯正霖去阿里检查交通路况,回程的时候要求我带路。拉萨的司机没经验,每天爆一个轮胎,四天爆了三个轮胎。阿里的两辆送行车每天贡献出一个轮胎,最后四个车还是缺了一个轮胎,只好两个车先走一段,到安全的地方卸一个轮胎,由另一辆车带着返回接应,反复轮换着才好赖从无人区里驶出来。回到拉萨,冯正霖感慨非常深,我乘机要求给我们阿里交通局买一辆生活用车,他当时就决定排除资金困难给一台东风货车。我喜出望外,立即把我的驾驶员留下,叮咛他挑一台最好的,披红挂彩开回来。我自己开了来时的小车,一路唱着“说句心里话”赶回阿里。心里想,哪怕千山万水,以后最好每回都让我去带路。
过去,阿里交通局每年的福利是发5根蜡烛,而其他好一点的单位能发几只羊。有了这辆车,我们又修了大门,盖了10间土坯商品房由工会租出去,后来逢重大节日,我们交通局也可以发两只羊了!我这个“两只羊局长”,很自豪啊
终于通了客车
阿里解放四十多年了,是全国唯一没有客运班车的地区,人员流动受到极大限制,返回阿里的干部在拉萨等车一等两、三个月不是稀罕事。我曾眼睁睁看着阿里的病人一点一点没了气息,援藏干部拿着家中父母病危的电报一等几十天,瞪着湛蓝的天空目光绝望。历届地委、行署及交通局都有开通客运的设想,但受到资金、道路和车辆的限制,始终没能实现。
阿里地区拮据的财政无法承担开通客运所必须的购车款。经呼吁,陕西交通厅毅然伸出援助之手,时任厅长胡希捷拔付资金39万元专款。1996年,买了第一辆车――五十铃中型豪华客车。我高兴呀,中午接了钥匙,我从北京开了就走,一口气开到西安才算踏实了。
没想到好事成双,陕西省公路局给阿里交通局配了一套办公自动化设备!电脑是最新的联想486,当时的设备处女处长朱景华,心细地连打印纸都给一包包装好码在纸箱里!陕西交通厅特地派专人同我一起去阿里送车送设备,当我激动的开车带回阿里,那是惊天动地的高兴啊。阿里地委书记、行署专员专门召集全地区科级以上干部开大会接收这些宝贝。从此,阿里也有了办公自动化,陕西交通人不仅修路搭桥买客车,还送来了新科技。
1996年10月19日,满载乘客,挂着大红花的客车在歌舞中缓缓从狮泉河镇出发驶向拉萨。为了安全稳妥,我又贡献出给我开车的驾驶员。客车每月发往拉萨1个班次,从此结束了全国地级行政区域不通客车的历史。
过了不久,又从成都买了第二辆车。第二年,我们把第一辆车高于买价卖给阿里其他单位,又用这笔钱从当时的汉中汽车制造厂定制了两辆东风底盘的客车。差了六万块钱,车提不出来,当时的省公路局计划处处长冯明怀说:“老李,你去提车。钱,局里来协调”,想方设法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难题!我把自己培训的驾驶员全部贡献出去开客车,这下阿里就有三辆客车了。
援藏三年,要说成绩,没有全国的援藏政策、没有陕西省交通系统的全力支持、没有当地的配合是不可想象的。要说困难,那比牦牛尾巴上的毛还多。但最令我自豪的是,无论我这个交通局长走在哪里都是最受欢迎的。所以,尽管当时有着种种困难,包括境外的分裂势力叫嚣“一个处级干部的人头十五万人民币”,都不能阻挡我们修路的脚步。正是这种陕西交通人走到哪里都受欢迎的底气,让我心怀火热骑马跋涉在阿里的大地上。
记者手记:在李喜会办公室里,记者看到他珍藏的资料。有当时陕西省省长程安东给援藏人员的亲笔信,满是殷殷期盼与层层惦记,也有当时担任陕西省交通厅厅长的胡希捷给李喜会的亲笔信,还有当时为了给援藏同志解决后顾之忧的陕西省公路局共青团成立的12名青年者志愿者名单。这个时候,记者突然想起艾青的两行诗:“为什么我的眼里满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