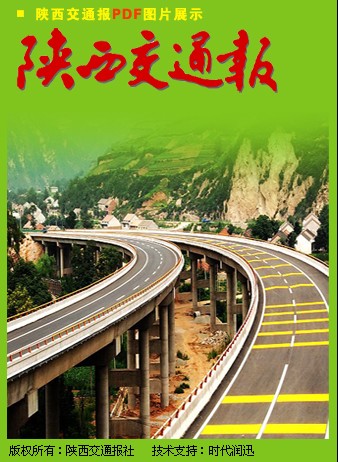今年的国庆长假,在家享受着“带娃七天乐”的时光,偶然点开微博,发现一众校友、同学都在转发着100多年前光绪帝批复奏折成立北洋大学的消息并由衷地祝母校生日快乐。终日混沌的我这才惊觉母校已经116岁,而距离父母、弟弟陪我坐着北上的火车去天津求学也已过去十个寒暑。十年,那一张张曾经在敬业湖畔的夕阳下笑得青涩、笑得无邪、笑得无比灿烂的脸现在都是什么模样?
2001年9月,环境工程专业两个班60个学生围坐在泛着点点波光的敬业湖畔,一个接一个地作自我介绍。晚风不时吹皱平静的湖水,湖上的求是亭回荡着我们的歌声、笑声,于是,我们在这里熟识,之后便有了很多关于敬业湖的故事。
自从跟着我第一次在学校寻找澡堂便迷失在敬业湖畔开始,同宿舍的小杨在今后四年的大学时光里再也不敢轻信我这个路痴所说的关于方向关于路线的一切。相反,她倒成了我的导航“手杖”,那是因为她身材娇小,走路的时候我总是喜欢把手搭在她的肩膀并嚣张地说:“喏,手杖的高度,刚刚好!”不管是上下课穿行在教学楼之间还是闲暇时漫步在校园中,我要么谈笑风生要么左顾右盼,不看路不看车,走着走着旁边的“手杖”同学就会一边拽我一边责怪:“往边上走,前面有车!”四年间,我一直“横行”,她一直“导航”,配合默契。
至今难忘跟小猴游走在校园的那个夏日午后。踩着敬业湖边的斑驳树影,迎面走来两个东南亚模样的外国人,年轻一点的拿着地图朝我们走过来,用并不熟练的英语问:这个地方怎么走?我瞧了一眼他手指的地点,沁园宾馆,心中窃喜:还好还好,这个地方我熟悉。一边点头一边在肚子里搜刮初中英语课堂上就学过的有关问路的那段情景对话,然后手指着学校的东南方一口气讲完去沁园的路线,对方点头表示感谢。刚一转身猛然发现大事不妙,我拉了拉身边的小猴:“完了,我刚怎么忘记沁园宾馆已经拆了?快,快把那俩人叫回来,别叫人家跑冤枉路!”小猴转身准备去叫,可我又纠结了:“拆了用英语怎么说?”一时间,我俩都木然……我们拼命在自己的词库里搜索,可两个人的脑袋偏偏同时短路,就在我又逵旨钡氖焙颍小猴已经拉回那两个东南亚人,淡定地说:Qinyuan is disappeared!(沁园消失了)东南亚人先是一怔:“disappeared(消失)”?接着豁然开朗:“oh,disappeared!”他笑着表示明白,我们长舒一口气。从那之后,每次说到这个关于disappeared的段子,众姐妹都边笑边赞叹小猴的“机智勇敢”。
敬业湖中心有座桥,连接着学校的南北两个图书馆。惭愧的是,那时候的我除了上课,要么就窝在宿舍里睡得天昏地暗,要么奔波在学生会的各个活动场地之间,要么就躺在宿舍的电视机、电脑前把热播的港剧韩剧检阅个遍……这样一来,留在图书馆的记忆真的寥寥。关于北馆,只记得我在那里的影音室看了岩井俊二的《情书》,对这部日本青春电影的代表作和片中清秀好看的男主角印象深刻。至于图书南馆,倒是它旁边的那条小路成了大学四年里我们最热衷的地方。这条小路不长,却直通隔壁的南开大学,两所学校的学生都把它叫天南街。天南街云集了各种小吃,烟雾缭绕的烧烤摊,热气袅袅的麻辣烫,大众餐馆的盖浇饭,一块一串的糖葫芦,果篦儿油条自选的煎饼果子,还有路口二胖子烧卖的叫卖声。
不经意,一边听着亭子里大二学姐学唱《浪花一朵朵》一边把手中的饼干捏碎“赏”给湖里欢快的鱼儿已是十年之前;而毕业前夕的最后一次组织生活,我们面朝西边的敬业湖围坐在北洋大学堂前,看着身边每一双友善的眼睛和每一张熟悉的笑脸我念着半个晌午写完的发言稿居然有点哽咽,这也已过去六年。
今年八月,从北京看完米兰德比,没有直接回西安,而是买了去天津的动车票,终于回到了阔别了六年的母校。很庆幸,那天下午有当年的室友同窗陪我一起。我们从住了四年的49斋宿舍楼走到学四食堂,再沿着敬业湖一直往西,随风轻摆的柳枝一如往昔,坐在湖边的石凳上,眼前分明还摇晃着那个当年在这里跟教我们街舞的体育老师勾肩搭背、姐妹相称的我……只是面前的图书南馆旁不再有那条热闹非凡的天南街,取而代之的是一排砖红色的教学楼和气派的综合实验楼。
时过境迁,一点文字,一点心情,给我那个刚刚过去的以母校为开端的十年,给记忆中所有与之有关的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