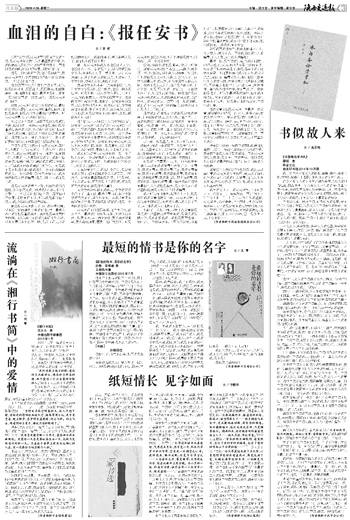《冰茧庵论学书札》
缪钺 著
碎金文丛
商务印书馆2014年10月版
我一向喜欢老派文人的做派,低调、谦逊、彬彬有礼,在温婉与谦和中透露着知识分子的学养和魅力。
许多老派学人的学术专著读起来空灵疏朗如咀嚼梅花,唇齿生香。学人与学人之间的手泽(先辈存迹)往来,虽然是吉光片羽终究值得把玩。在这些笔墨中,流露出来的不仅仅是学者们的思想片段,更有中华文化的密码,中国文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书似故人来。展玩书信,可浓可淡的笔墨,于不经意间传递着温暖,以及文人间书信来往的讲究。虽然时间久远,慢慢读来,如故人对谈。字是人情绪的表达,一笔一画,都牵动着书写人的内心情感,拨动着看字人的心弦。其实,书信之中,撇开内容不说,总会有很多小细节让人感动。
老式文人,讲究礼数,讲究对人的尊重,讲究谈吐文雅而不唐突,在没有短信、电话、微信的年代,书信是最主要的通讯方式,也是文人们传递问候,表达情感,切磋学问的最好载体。
上大学时,老师给我看了许多他收藏的前辈学人之间的笔墨往来。不仅字写得好,文章也写得好。老师说,这些学人之间的通信是她的重要收藏,小小盒子上,云纹已经被摩挲得掉光了。一封封短短手札,纸片已经泛黄,墨迹已经模糊,细细读来,还是那一派老式的风雅。老师说:“短短一尺素可传万里情。已故学人的书札实际上是一股可润心田的清泉。”吾辈愚钝,老师的话虽然记住了,但总也品不出其中的味道……
这些年,文人的书信读了不少,《增文正公家书》《海明威书信集》《傅雷家书》,涉猎的书信集不下五十种,但是却很少让我真正的感动。
前几年研读诗词时,方才知道缪钺先生这样一位学术前辈。于是力所能及地收集先生所有书籍,碎金文丛出版的《冰茧庵论学书札》便出现在我的书案之上。读读这位老学者的书信集,为自己浅薄的思想充充电,也为疲惫的心找到一个可以短暂栖息的港湾。
关于缪钺先生,恐怕很多年轻人都未曾听说过。缪钺先生的学问体大精思,在史学、文学、诗词、书法方面造诣非凡。先生与同辈学人、晚辈学人之间的通信,也颇为可读。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不得已闭门读书,在展读先生诗词的同时,再次细度了先生之孙缪元朗编辑的《冰茧庵论学书札》。上下两本小册子中收录了缪钺先生上百封书信,友朋中多为文史名家,如吴宓、刘永济、陈盘、劳干、杨联升等,内容广涉史籍考订、诗词品评及学界之书人书事,深具价值。
细细读来,不仅让我这个对书信已经很陌生的人再次感受到书信的魅力,也感受到老一辈学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谦和的为人处世做派。
先生在书信中对收信人的称呼常常用教席、史席、学案这些文雅且让今人陌生的称呼,对方不论年长、年幼均以“弟”自居,且“弟”字往往小一号。书信谈论的大多为诗词、历史、教育以及文人之间的掌故。这些书信文笔简洁、用词典雅,笔墨疏朗,每一封书信均可做学术美文细细把玩。如明清小品一般,在淡淡的笔墨中流露出老学者的家国情怀与个人志向趣味,传递着一个学者的心胸襟怀和修为。
我生也晚,活了三十多年收到和寄出的书信不超过三十封,常常以读书人自居的我,想到这些不禁后怕。扪心自问,自己会不会写信,能不能用书信表达胸臆,真的有点胆怯。
读缪先生书信的同时,也读了几位时下学者的书信,虽然用字、用词依旧讲究,但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与缪先生的书信对读,让人内心徒然升腾起一种无奈之感。
唐代诗人李冶的《结素鱼贻友人》:“尺素如残雪,结为双鲤鱼。欲知心里事,看取腹中书。”我想那些期盼收到缪钺先生书信的人恐怕也有这么一种感觉。
在手工时代,书信本事就是一种手工作业。在安静的书房中,一笔一画静静地写字,每个笔墨都流露一种情愫和情怀。贴邮票、投递邮箱,然后交给时间,让最真切的语言慢下来。
我听说一个爱斯基摩人的故事,据说在天寒地冻的极地,人们一开口语言便被冻住了,于是对方只能把语言带回家,在炉子上慢慢烤,一句一句地听。这个故事我很喜欢,很浪漫,如书信一般,传递的是被固化的语言,也是一种缓慢的、优雅的浪漫。
香港作家董桥先生说,他与老友之间,依然采取手工书信,即便是通过传真发送,也要再邮寄一次。见字如面,我想,通电话、发微信,恐怕没有这种感受吧。话题扯得有些远了,缪钺先生这些书札不仅是思想的载体,连接学者友谊的介质,更可作为先生治学的学术心传。读完《冰茧庵论学书札》,似乎又把我拉回了那个笔墨生香的年代。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书信,所传递的不仅是语言,更是远方的诗意,在书信时代终结的今天,写信、读信,自然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作者供职于汉宁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