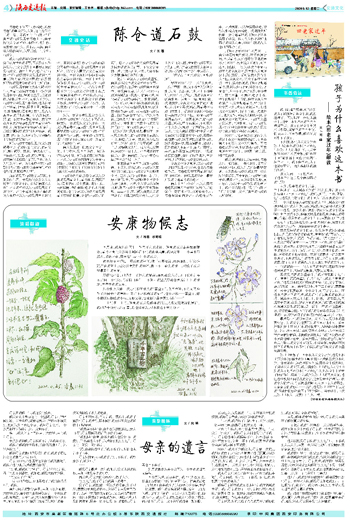母亲走的那一年,我还没有成家。
那天距离中秋节还有一个星期,母亲精神略微好转。医生答应,如果近两天精神状态继续向好,就可以先回家过个节。我替母亲高兴,一个多月都在医院待着,她一定憋坏了。
晚上,我让父亲回去休息。病房里,只有我和母亲。
十点多的时候,母亲说睡不着,让我关了灯。
我说:“那我倒些热水,给你洗洗脚吧”。她轻声说“好”。
那时母亲的脚已经是浮肿的了,我的手滑过她高高的脚背,心疼不已。
母亲叹口气:“这现在还让你给我洗脚呢”。我说:“这有啥,以后我常给你洗”。
“好哦,那我可有福了”。母亲轻轻笑着说。眉目间却不时紧锁。我知道,那是病魔在作怪。
“背又疼了?”“嗯”。
止疼药已经吃过,不能再吃了。“我给你揉揉吧”。我说。
窗外,白天的繁华落尽,只剩下灯火阑珊。病房里很静,每个房间都似乎飘荡着一个家庭的无助与悲伤。对于绝症,病人与家属往往心照不宣,面对面却不忍心触及敏感话题,展开的每一次闲聊都成了珍贵的道别。
母亲坐在床边,背对着我。黑暗中,我的手触及到母亲的后背,原本微胖的身体在浅色的睡衣中已显单薄。
“我其实不担心你,你外婆以前就说过,女大自巧”,母亲用微弱的话语打破了沉寂。
“我就担心你爸,你说他那人也没个自己的爱好。”“小吴这人不错,以后你们就好好过”。母亲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
“妈,你别说这些了。”我打断了她,眼泪也跟着掉了下来。
母亲从前面拉拉我的手,“好,不说了。我舒服多了,睡觉吧。”
……
那是母亲最后一次和我聊天,没了儿时的说教,只剩下满是牵挂的叮咛。
两天后,母亲病情突然恶化,撒手人寰。
“好好过”,成了母亲给我留下的遗言。
没了母亲,我就像一棵飘摇的浮萍,失了根基,常常处于恍惚的状态,觉得母亲只是出去散步了,或者正在厨房洗菜做饭,又或者清晨赖在床上等她不厌其烦地催促我起床。恍惚之后,已是泪流满面,原来一切不过是自己的臆想,母亲再也回不来了。
岁月的脚步从来不会因为一个生命的逝去而停滞。
四个月以后,春节来临。我回到外婆身边,长辈们按惯例忙碌着准备团年饭。临窗的街道上,车辆照旧你来我往,行人依然穿梭不停,生活一切如常。那年的春晚如期直播,舞台上,灯光闪耀,毛阿敏正演唱一首《天之大》,歌词动情,撩拨人心,把我对母亲的想念放大到极致。“思念,何必泪眼”,母亲一定不希望我这样一蹶不振。
春节过完,又是新的一年。站在新土堆就的坟前,我与母亲告别,决定开始新的生活。
一年之后,我经历了结婚、生子、工作、买房,一切井然有序,仿佛母亲就在身边一样。
老家有种说法,家有长辈去世,要过三年才会真正地离开。我想母亲大概也是守护了我三年。母亲总这样为我操碎了心。她曾抱怨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学业上帮不了我,便要生活的每个角落给我无微不至的爱。
2005年我刚工作那会儿,母亲第一次瞧见我租住的房子,心疼地直咂嘴:“这顶层夏天得多热啊,洗衣机都没有,床这么脏得赶紧换了……八月份,趁着我上班,她和父亲冒着火辣辣的太阳跑东跑西,一天功夫不到,小到针线、水果刀,大到电视洗衣机,竟把屋里该置办的都置办了。
我跟母亲开玩笑:“你咋不把老家给我搬来呢”。母亲白我一眼:“好日子都是自己过的,家就要有个家的样儿。”
那晚母亲睡在我的身边,担心着我在省城的生活。我把母亲的脖子一楼,亲昵地在她耳边说,“你要相信自己闺女嘛,等我在省城站稳脚跟了,你跟爸就一起过来跟我住”。
母亲听罢,眼睛笑成了弯弯的月牙,“那感情好,我们可等着享你的福呢”。
只是,那样的幸福已成枉然,母亲的笑只留在了那个夏天的夜晚。
日子随着我的年龄增长一天天热乎起来。我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母亲的一些生活习惯,学着她孝敬长辈、疼爱孩子,往平淡的生活里积攒幸福。
这大概就是母亲说的“好好过”吧。不求我们大富大贵,只要一家人居有定所、平安健康、其乐融融,就比什么都好。
我的衣柜里有一件绿色的T恤。那是母亲那年来省城治病时给我买的,当时觉得那绿色有些土气,还不肯穿。母亲走后,我在衣柜里再发现它,突然觉得绿色跟那句“好好过”不是一个期待吗?即使母亲不在身边,我们也要脚踏实地过好每一天,让日子有希望!有奔头!
这几年,我的梦里不像前些年那样频繁地梦到母亲。家里老人说,那是母亲知道我们把日子过顺当了,放了心。我突然明白,好好生活才是对逝去的母亲最大的慰藉。
我把这件T恤用纸袋封存放置衣柜里,每年的入夏和入秋时节整理衣柜时,总要拿出来看看,越发觉得,母亲原来是有大智慧的。